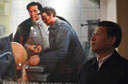暮色由淡到濃,不久就黑下來了。館裡燈火通明,姑娘們剛剛練完球,汗水濕透的衣衫緊緊地貼在身上。白色的排球撒滿一地,姑娘們正彎腰撿拾著。“誰還想加練一會兒?”教練袁偉民沖著這群疲憊不堪的姑娘大聲問道。“我加練一會兒!”一位靈巧秀氣的姑娘抬起頭來,搶先回答。她叫陳招娣,家住西子湖畔,是一位典型的杭州姑娘。
——浙教版初中語文課文《苦練》
她是初中課文《苦練》裡的精神代表,她是老女排五連冠的象征符號,她還是共和國體育界的首位女將軍﹔她身上有杭州姑娘的靈氣和堅韌,也有老女排獨有的不畏強敵、奮力拼搏的氣質,她的名字幾乎激勵了數代中國人。
但這一切都隨著一條微博隨風而去。
“媽媽走好,那個地方沒有疼痛,沒有疾病,隻有開心。還有兩天我就26歲了,你又一次騙我,我不恨你,媽媽我依然愛你。”昨日14時59分,一位名為“加菲貓小貓”的網友發表了一條微博,她是杭州籍女排名將陳招娣的女兒郭晨。隨后噩耗傳來,陳招娣因肝癌晚期(直腸癌轉移)搶救無效,於昨日下午在北京逝世。
“獨臂將軍”的榮耀
很多的“70”后、“80后”乃至“90后”認識陳招娣,都是因為本文開題的那篇《苦練》。
該文描寫的場景是,在一天的大運動量訓練后,所有隊員都累趴下了,隻有陳招娣主動咬牙加練了15個好球,最后她骨子裡的這種倔強,讓教練袁偉民都贊嘆不已。
而在昨日記者的採訪中,無論隊友、教練還是親戚,都會不約而同地提起陳招娣這份堅韌。
1955年,陳招娣出生於浙江杭州,曾就讀於杭十中,1973年入選八一女排,1976年入選袁偉民執教的女排國家隊,擔任二傳和接應,並成為了中國女排沖出亞洲、走向世界的核心成員。
1981年,陳招娣幫助隊伍獲得了世界杯冠軍,這是中國女排的第一個世界冠軍頭銜。隨后,她又以主力身份率隊連奪1982年世錦賽冠軍和亞運會冠軍。
作為中國女排兩奪世界冠軍時的主力接應,性格倔強的陳招娣不但技術出色,二、三號位進攻手段多且防守出色,她的頑強拼搏更是在球場上享有盛譽。
1978年,從國家隊回八一隊打全國甲級聯賽時,陳招娣左臂橈骨首次受傷。次年6月亞洲俱樂部冠軍日本日立隊訪華與中國隊在太原展開激戰,當時陳招娣在比賽攔網時被隔網而對的奧島圭子大力扣中受傷部位導致橈骨骨折。兩個月后的第四屆全運會,陳招娣用繃帶吊住左臂,帶傷出戰單手比賽,自此她就有了“獨臂將軍”的美譽。
“我們來世還做隊友”
作為曾並肩作戰的杭州市體校隊友,前浙江女排隊員陳軍和陳招娣的關系一直很好,近些年又因為工作上的原因,一年常會見上好幾次。
陳招娣的病情她早已得知。“去年夏天我們在廈門打‘元老杯’的時候,她還過來頒獎。后來11月在嘉善打女排聯賽,我知道了她的病情。今年大年初二,我不敢給她打電話,給她的小姐妹——八一體工大隊副大隊長沈散英打了一個,說是已經出現腹水了……我們也有一些心理准備,可沒想到這麼快,舍不得,真的舍不得……”電話那頭,陳軍低沉地說。
“招娣是1971年入隊的,我是1972年,比她晚一年。不過她當年就去了北京(入選了北京體院青訓隊),我們在一起練的日子不多,但打的比賽很多。”陳軍回憶說,“她的身體條件其實不好,身高1米73,但是非常努力,打球也靈光。防守非常棒,什麼球都能救。”
雖然陳軍已經退休,但在心裡,對這位師姐的敬佩絲毫沒有因為歲月的流逝而減弱:“如果說女排精神是中國體育的一面旗幟,代表了銳意進取和頑強拼搏,那陳招娣起碼代表了三分之二的老女排精神,她的堅持、刻苦絕對是平常人無法想象的……快50歲的時候還在考研究生,我說她‘招娣,干嘛這麼拼命’,她就是笑笑……”
噩耗傳開,國家隊的老隊友郎平也在第一時間表達哀思。在其微博中,她深情地說:“親愛的招娣,上月去探望你時我們還在討論排球,我執教的每場球你都很關心並提出建議。你對親情友情都那麼執著。還記得1981年我們奪取第一個世界冠軍那次,咱倆是室友,決賽前你腰傷復發但咬牙堅持拼完五局,是我們扶著你走上領獎台的,你頑強的拼搏精神永遠激勵著我。”
“做了少將,還回杭州做比賽仲裁”
一篇《苦練》讓所有人都知道了女排精神和陳招娣,但還有很多人不知道,陳招娣還是共和國體育界裡的第一個女少將。
1993年,陳招娣回到總政文化體育局工作。2006年7月,她晉升少將軍銜,成為體育界的首位女將軍。
當年,王治郅為打NBA不回國,引發了巨大轟動。鮮為人知的是,后來大郅能夠順利回歸國家隊,都是陳招娣的功勞。因為八一體工大隊隸屬於總政部文體局,局長當時正是陳招娣。據說,當時對王治郅的處理決定已經擬好了,但被陳招娣頂著壓力壓了下來。
就是這樣一位敢作敢當的女將軍,面對家鄉情卻表現出無比的溫柔和隨和。
“前幾年,浙江有個排球比賽,我請陳招娣回來做比賽仲裁,她二話沒說就答應了,一點架子都沒有。”陳招娣當年在體校時的教練、后來的浙江農大體育部主任李趙來想了一下:“對,她那時就已經是少將了。”
“我記得她剛入隊的時候,朴素,善良,很聽話。”李趙來回憶說,“她是杭州人,但家裡條件不好,所以很能吃苦。當時體委維修房子,她媽媽就在體委做小工,我和她聊過,也是個很善良的人。”
“姑姑說,退休了一定要回杭州”
或許是因為家庭遺傳原因,陳招娣的父母、2個姐姐以及弟弟均患類似病症身故,現今在杭州的親屬,隻有一個侄女陳素琴,目前在一家體育媒體工作。
“前段時間去看姑姑,她的病情就已經很嚴重,都認不清我了。”昨天晚上,記者聯系上了陳素琴,“即便最后階段,姑姑也很頑強……4號我會去北京,送姑姑最后一程。”
回憶起姑姑,陳素琴有很多話說,“姑姑是個做實事的人,從不夸夸其談,生活也很節儉。她經常教育我姐姐(陳招娣女兒郭晨),有用的東西就買,不該買的不買。”
“對我,她也很關心,讀書時經常打電話來問我的學習情況。工作了,常會打電話給她在體育局的老朋友和隊友,詢問我工作上的問題。”陳素琴說,“姑姑曾跟我說過,退休了一定會回杭州來養老。”
往年每到三四月份,陳招娣都會回杭州住上一陣,因為這段時間是杭州最宜人的時節,但今年,陳素琴再也等不回自己姑姑了——而我們,同樣再也等不到那個一次一次的飛身救球,一次一次帶傷參賽的排球女將。
再見,招娣。
再見,我們那段關於拼搏、堅韌和榮耀的記憶。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